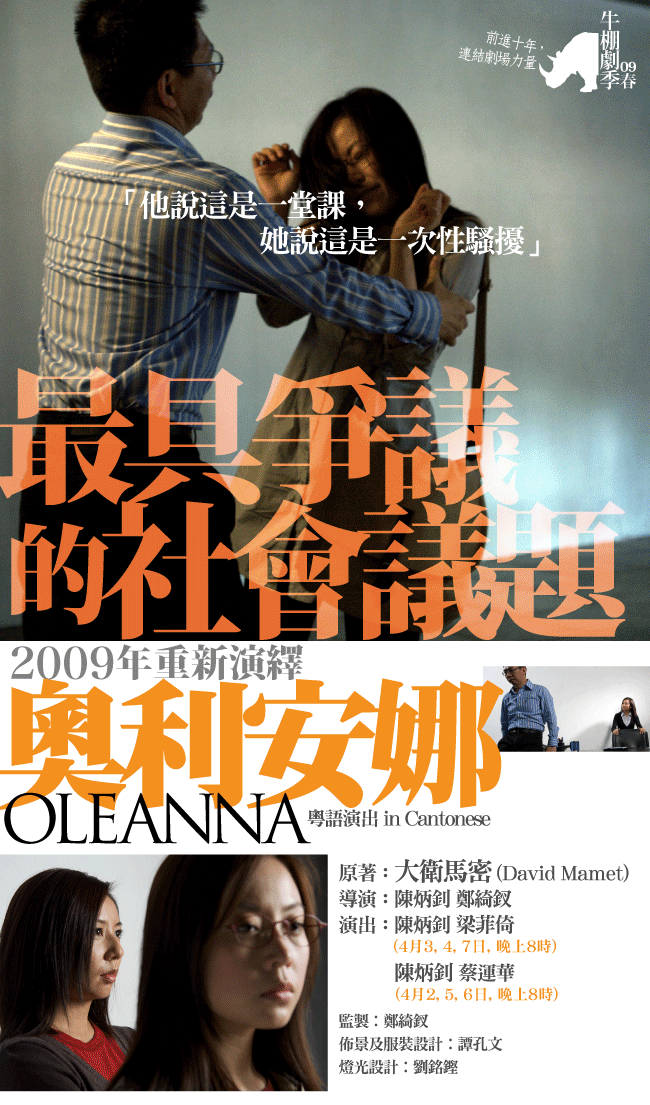劇場讓我們走在一起。
2月27及28日文化中心劇場上演香港藝術節節目《失衡世界》,編舞和音樂是來自巴勒斯坦的Samaa Wakim和Samar Haddad King。她們用身體和音樂去體現銘刻在回憶深處的戰火印記。筆者看的是28號晚上,差不多滿座,觀眾來自五湖四海,阿拉伯觀眾很多。自己見識少,第一次和大量阿拉伯觀眾同席,他們相互認識,互叫名字,如參加一次家庭聚會,坐在前面的兩位女士都戴上巴勒斯坦方巾,心繫支持家鄉的熱切。
演出的舞台設計簡約,就是一條綠色帶子橫架在台,沒有花樣燈光,沒有巨製投映,單靠現場音景(soundscape)主導情感空間及移動想像,當然,還有舞者的身體。編舞的創作概念很純粹:「你唱歌,你跳舞,你大笑,嘗試從中尋找平靜,但現實終究什麼都沒有改變——你依舊在動盪不安的世界裏,拼命在一條搖晃不定的幼線上尋找平衡。」「我嘗試將現實的恐懼化為肢體動作。」巴以衝突幾十年未息,以軍攻擊下的加沙地帶天天直面死亡,一切生靈活在恐懼下。兩位舞者把成長的惶恐具象為演出,而我們即使沒有戰火,日常生活也在幼線上奮力尋找平靜,共感脆弱。因此,當舞者面朝地下伏在線上做類似游泳又似逃跑動作,配上現場女聲不斷倒數,28、27 跳接13 再4……3……然後從頭再由29開始,體現掙扎的分分秒秒,逃離迫切又徒勞,循環不斷,誰都明白,心在一起震顫。還有走鋼線的平衝和失衝的動作等,都直接明白。
不過,在表演性上,的確未能滿足我此等麻煩的觀眾,如一條幼線分隔了台上虛實正負空間,好玩多變,卻沒有善用。舞者的動作變化不大,仍受限於專業訓練而來的範式要求,失衡仍是某種控制下的美。情感和想像多由聲音帶動,而不是劇場空間。不過,Samar Haddad King現場製造的聲景很精彩,如一段二人簡單地用口哨來模仿空襲警號及炮彈聲音,舞者頭部及上身隨聲音滑行,很能讓人感受滿天軍機壓頂的恐懼。此外,還有祖母的溫柔細語,夾雜着汽車的煩躁響咹、茶館的歡快舞曲、機關槍聲霹靂不斷,又有清脆的鶯鶯雀聲,都在推動情景的起落。我更傾向以身體美學(Somaesthetics)來看舞者動作的演出,就是身體如何回應及感知外界的變數,而不是傳統的舞台技法。
應有的國際關懷
既然看的是身體變化,現場觀眾的動能也非常好看,特別是完場時,近乎全體一起站立鼓掌,更有一名本地年輕人揮旗支援,隱約聽見有人叫「free Palestine」,久違的集體歡快,剎那充盈劇院,大家像球迷般不分你我團結一致。同看的朋友慨嘆說,這才是國際文化都會應有的國際關懷。
只是,散場後,一切如常?劇場文化始終離不開商品化邏輯,我們是否只是買得起門票的優越消費者?我們在消費別人的災難嗎?「Mind your privilege」幾個字不斷敲打心臟。如何穿越被動消費者的定型角色?想起班雅明給我們《拱廊街計劃》的通道(passage)意象,如何打開多樣的通道,不停留在感傷,不固滯在簡便的消費?如何為自己穿越創造條件?
主動認識,增長知識是否最低的要求?舞蹈本身也可以是理解文化內核的起點。先是好奇來自歐美的當代舞在巴勒斯坦的發展,原來一直有很多爭議,因為當代舞就是一場對(西方)現代化的想像、國族身分建構、性別定型的糾纏。可以想像巴勒斯坦的民族舞Dabkeh,一直跟隨戰火、宗教(基督教及鄂圖曼帝國佔領時期的伊斯蘭教)、土地政策(農民和社區舞蹈)、後殖文化而改變,還有跟鄰近中東地區,如土耳其、埃及、黎巴嫩等地的肚皮舞互動、協商、挪用而成。從舞蹈發展來看,巴勒斯坦政治及文化脈絡非常龐雜。由澳州學者Nicholas Rowe寫的Raising Dust: A Cultural History of Dance in Palestine有很詳細分析。這位學者也是編舞家,曾在巴勒斯坦佔領區駐留8年,在難民營跟不同舞者及藝術家合作,有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訪問及歷史脈絡的爬梳,大大豐富對中東舞蹈的認識。如何在東西文化夾擊,傳統及現代當中找出文化身分新路,正是作者提出的post-Salvagism,看來很合香港參考。
此外,巴勒斯坦儘管物質短缺,仍然不懈搞舞蹈節,跟國際舞台接軌,建構和世界對話的可能,如已有十多年歷史的Ramallah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al,知名如Akram Khan Company、BalletBoyz、Protein Dance都曾出席,看它們的主題如「邊界故事」、「中東的身體」都深感高度脈絡化,不是泛泛而動,它們面書首頁圖像寫着「我身上有千個故事」很有感染力(www.facebook.com/RCDFpalestine)。
本地藝團打開國際文化對話
這種用表演藝術來打開國際文化對話,香港也有非牟利藝術團體「流白之間」在努力,除了去年創建了全球性的「烏克蘭讀劇籌款活動」外,也曾在去年9月初,帶着舞踏舞者謝嘉豪(Tomas)的作品,參加烏克蘭第一個藝穗節。它的標語是「Festival For The Brave」,可見當地藝術家的堅定及勇猛。早前曾參加他們的分享會,看了一套由美聯社攝影記者拍的紀錄片《馬里烏波爾戰火20日》,對烏俄之戰有更多直接的感受,也銘記Tomas的一句話:「烏克蘭不需要我們的同情,而是我們的同行。」
如果文化交流不止是一個商品化的口號,也不輕省成為行政工具,我們都要好好考量如何以表演藝術或其他方法建構通道,穿越失衡時代,可能要更多個「流白之間」?更多知識上的開拓?想起Richard Sennett的書Together強調我們愈來愈碎片部落化,得要磨練對話、聆聽及回應的能力,才可以談合作。如何建構有創作力的「在一起」,如何重拾感同身受的感應,如何增厚歷史感的光照?願同行,持續尋找開創通道的方法。